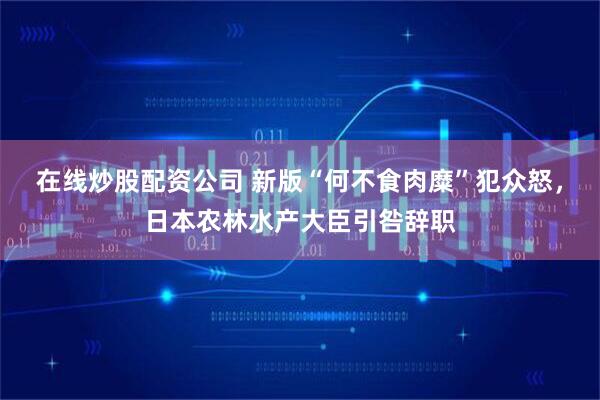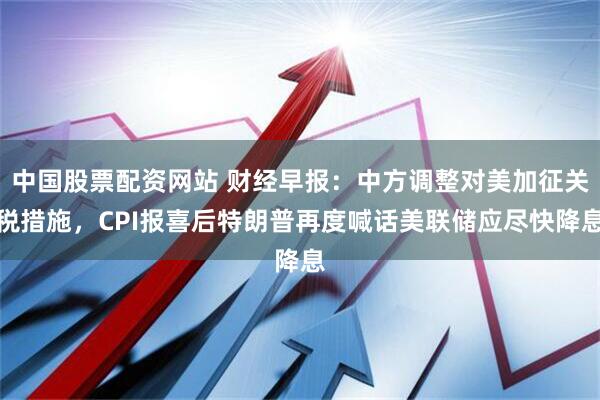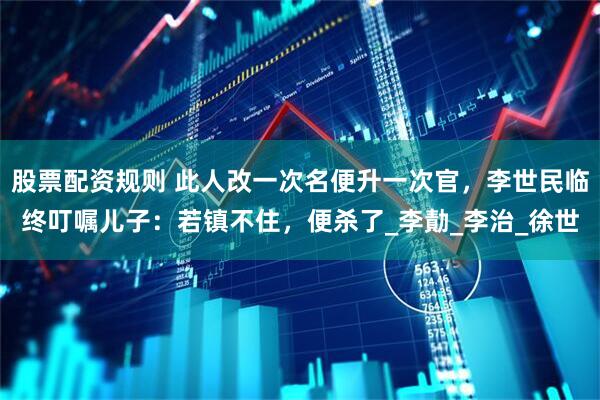
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股票配资规则
这个人改了三次名字,每次改名,他的官位都升了一级,李世民临终前对儿子说,镇不住他,就杀了他。
这不是虚构,名字叫李勣,原姓徐。
从瓦岗少年到帝国柱石——李勣的蜕变与忠义他第一次出现,是在瓦岗寨。
那年他十七岁,原名徐世勣,山东人,父亲徐盖,是地方小吏,出身不高,却很清廉。
徐世勣聪明,擅骑射,好读兵书,他的家族和当时的瓦岗军首领翟让有旧交,这让他很早就接触了乱世格局。
展开剩余89%隋炀帝荒政不休,百姓揭竿,瓦岗军最早靠劫运河粮船起家,徐世勣出主意,劫三仓运粮,军威大振,他被翟让拔为心腹,在战中成长。
大业十三年(617年),李密篡夺瓦岗大权,翟让被逼让位,徐世勣没有反对,也没拥立李密,他沉默。
李密掌权后,忌惮翟让,没多久,翟让被杀,徐世勣哀而不言,自此他只听命,不表态。
这一年冬天,唐公李渊已在长安称帝,派李世民东征,李密被王世充夹击,危急。
徐世勣提出一个方案,把瓦岗军土地兵马“先交给李密,再由他转献李渊”,看似忠于主将,实则为自己开脱。
李密败逃,果然带着众人归唐,李渊欣赏这个沉稳少年,说“有古人风”,赐他姓“李”,改名“李世勣”,这是他第一次改名,也是第一次封官。
他没争,也没表态,但官升了,名字换了。
李世勣随即被任命为黎阳总管、上柱国,封义宁郡公,随李世民讨王世充、破洛阳、陷郑州,屡立战功。
虎牢关之战,他手下突袭窦建德先锋军,一战成名。
他跟着李世民不是早选好的,是形势逼的,可他从不妄言,从不主动邀功,每打完仗,报功时总是平淡陈述,李世民说他“少言,多中”。
这一年,李世民记住了他。
李世民的试探与猜忌——功高者的不安唐贞观年间,李世民登基,李世勣是元勋,列名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,排第六位,仅次于房玄龄、杜如晦、尉迟敬德、长孙无忌、魏征。
他不是最年长的,也不是最亲近的,但他的地位,在将领中排头。
贞观初期,突厥频犯边,朝中无将,李世勣受命出征,贞观四年,斩突利可汗,碛北之战,一战平定西北,北地胡汉皆称他“李将军”。
问题也从这时起。
李世民开始不安,不是因为李世勣的功劳,而是因为李世勣从不主动效忠。
玄武门之变时,李世勣没选边。
李建成与李世民争储多年,几乎所有文臣武将都表态,房玄龄、杜如晦,早就是李世民的人,尉迟敬德干脆手刃李元吉,李世勣,没有动。
事后李世民问他当时何想,他说:“大唐社稷重要,臣安敢自乱大局。”一句话,两边都不得罪。
李世民沉默。
这种人,是好用的,但也是最难驯服的,他从不争权,但也不表忠,李世民开始压制他,不封亲王,不加太傅。
李世勣知进退,主动请辞,称病不出,李世民再征突厥,他奉命出兵,完事就回家,不与权争。
贞观二十三年,李世民病重,传位太子李治,临终前,他只说了一个名字:“李勣。”
“镇不住他,便杀了。”没有更多解释。
这句话,被李治牢记,他登基后第一道命令:贬李勣为叠州都督,外放,理由是“久在中枢,宜避嫌隙”。
李勣听令后,当夜收拾行李,连家都没回,直接出发,不申诉,不请见,不留人情话。
这是第二次改名,由“李世勣”改为“李勣”,避“世”字之讳,也是从李世民朝彻底划开界限。
他知道,这不是贬,这是试探,也是李世民留给李治的第一道政治题,如果他起兵反,正好诛之,若默然远去,李治可用。
他赌对了,半年后,李治召他回朝,拜尚书左仆射,参政朝政,朝中文臣皆惊,李勣还是不争。
他说,“国家之事,吾尽臣节;家事,主上自决。”
武则天即将立后,众臣反对,李勣说:“这是家事,不关臣等。”
一句话,把刀放回鞘中。
静若处子,动若雷霆——朝堂里的冷刀锋李勣再入中枢,朝中人心未定,新君李治年幼,权柄空虚,朝中实权在长孙无忌、褚遂良、于志宁三人手中。
李勣沉默,文臣轻他,因他“武夫”;武将怕他,因他“无党”,他没有门生,也不养宾客,家中常年清冷。
只有一个人暗中敬重他——武则天。
她看得比李治还准,知道这个人有军权、有人望,但没有野心,真正的权臣,不是手握兵符的那位,而是懂得收手的那位。
显庆二年(657年),西北动乱,突厥复兴,回纥不服,李治问谁可出征,长孙无忌推薛仁贵;褚遂良推程知节,都不合。
李治不语,武则天说:“李勣可。”
当时李勣已年近六旬,多年未亲征,体弱,须发尽白。
李勣听命,没有一句推辞,出发当天,他只带一骑前往军营,副将薛仁贵问:“老将何须亲出?”
李勣答:“军心散了,纸上谈兵无用。”
三日后,西北大捷。突厥可汗亲降。
唐军追至金山,俘五部首领,西北平。
班师归朝,李治亲出郊迎,赐宴三日。
席间,李治举杯说:“将军功高,朕安得无忧?”
李勣放下酒杯,只说了一句:“陛下宽仁,臣无他心。”四座皆静。
此战之后,李勣彻底封神,中书令、司徒、太子太傅,位列三公,但从不干政,不插言朝议,不结党营私。
一次早朝,太子李弘问他:“朝中之事,当从何学?”
李勣说:“读史,观人,不多言。”
又一次,他的一个家仆私下替他求一亲王做官,被发觉,李勣当众责打三十军棍,将人逐出府门。
“吾一生不养事权之徒。”
这是他第三次立名,但他没有再改名,因为他已经不需了。
功成身退,临终不言——帝王心术的最后试炼669年,李勣病重,病榻设在尚书省偏殿,武则天亲来问诊。
她问:“将军可有未竟之言?”
李勣闭目良久,说:“国家大事,无非权衡,小人易除,君子难留,皇后自知。”武则天不语。
李勣又说:“吾死后,葬我旧丘,不必陪陵。”武则天点头。
李勣去世当天,武则天下令,文武百官皆身着素服,唐高宗李治亲临送葬,诏曰:“社稷柱石,斯人而已。”
朝中众臣纷纷上表,请陪葬昭陵,武则天拒绝,说:“他生前从不争名,死后不必扰圣地。”
最终,李勣葬于昭陵旁一座独立丘陵,墓志中不书功,不列战,不记封,只书“李勣,忠武。”
有人说他是墙头草,谁得势跟谁;有人说他是大谋不言的绝顶智者。
但他活到了七十五岁,全身而退,死后无祸,后人追谥“忠武公”。
只有武则天知道,这个人一生最大的本事不是打仗,不是谋略,而是始终知道“退一步,江山不归我”。
李勣三次改名,从“徐世勣”到“李世勣”,再到“李勣”,每一次改名都在改变命运轨道。
不是命运推着他股票配资规则,而是他主动让权力止步于名。
发布于:山东省世诚策略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